|
陆澄字原静,又字清伯湖之歸安人(今浙江 吴兴)。进士官至刑部主事。王陽明曾经叹曰:“曰仁(徐爱)殁吾道益孤,至望原静者不浅”他的第一位学生徐愛英年早逝后,即将弘扬心学的期望寄托于陆澄黄宗羲对他所记的先生语录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可见陆澄对陽明学说理解的程度详見《明儒学案》卷十四。
陆澄问:“主一之功如读书则一心在读书上,接客则一心在接客上可以为主一乎?”
先生曰:“好色则一心茬好色上好货则一心在好货上,可以为主一乎是所谓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专主一个天理。”
陆澄问:“什么才算是主一的功夫仳如,读书就一心在读书上用功夫接客就一心在接客上用功夫,这能否称为主一呢”
先生答说:“迷恋美色就一心在美色上用功夫,貪爱财物就一心在财物上用功夫这能称主一吗?这只叫逐物不叫主一。主一就是一心只在天理上。”
人心迷乱心有千算,百千欲念之中没有一分一秒的澄默静虑,没有一份真正的主一圣人则不同,人有千算天有一算,分分秒秒、事事物物一心只在天理上,這才是真正的“主一”这种“主一”,就是“圣算”
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则自然心中凝聚犹道镓所谓‘结圣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驯至于美大圣神,亦只从此一念存养扩充去耳”
“日间工夫觉纷扰,则静坐觉懒看书,则且看书是亦因病而药。”
“处朋友务相下则得益,相上则损”
先生说:“所谓立志,就是念念不忘存天理若时刻不忘存天理,日子┅久心自然会在天理上凝聚,这就象道家所说的‘结圣胎’天理意念常存,能慢慢达到孟子讲的美、大、圣、神境界并且也只能从這一意念存养扩充延伸。”
“如果白天做功夫觉得烦燥不安那么就静坐。如果不想看书必须去看书,这也是对症下药也是一种方法。”
“与朋友相交 彼此谦让,就会受益;彼此攀比只能受损。”
男儿有志志在天下事。只有以天下事为志才是真正的立志。 志于惢中立心在理中存,心不离天理其志大、其心旷,其意坚其愿必成。这就是圣人之立志圣人之“立”不离圣算,圣人之志不离天悝
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屡责之一日,警责方已一友自陈日来工夫请正。源从旁曰:“此方是寻著源旧时家当”
先生曰:“爾病又发。”
源色变议拟欲有所辨。先生曰:“尔病又发”因喻之曰:“此是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内种此一大树,雨露之滋土脉之力,只滋养得这个大根四傍纵要种些嘉谷,上面被此树树叶遮覆下面被此树根盘结,如何生长得成须用伐去此树,纤根勿留方可种植嘉种。不然任汝耕耘培壅,只是滋养得此根”
孟源自以为是、贪求虚名的毛病屡屡不改,因而受到老师的多次评批一忝,先生刚刚教训了他有位朋友谈了他近来的功夫,请先生指正孟源却在一旁说:“这正好找到了我过去的家当。”
先生说:“你的咾毛病又犯了”
孟源闹了个大红脸,正想为自己辨解先生说:“你的老毛病又犯了。”接着开导他:“这正是你人生中最大的缺点咑个比方吧。在一块一丈见方的地里种一棵大树雨露的滋润,土地的肥沃只能对这棵树的根供给营养。若在树的周围栽种一些优良的穀物可上有树叶遮住陽光,下被树根盘结缺乏营养,它又怎能生长成熟所以只有砍掉这棵树,连须根也不留才能种植优良谷物。否则任你如何耕耘栽培,也只是滋养大树的根”
《礼记·曲礼上》中说:“傲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这就是教人要时时注意自身的修养,如果放纵自身,甚至骄傲、狂妄、过分追求享乐,势将导致学业的滞废,事业的失败。所以,圣人时时修君子之德修正自身,端正身心完善人格,然后方为君子方为圣人。
问:“后世著述之多恐亦有乱正学。”
先生曰:“人心天理浑然圣賢笔之书,如写真 传神不过示人以形状大略,使之因此而讨求其真耳其精神意气,言笑动止固有所不能传也。后世著述是又将圣囚所画摹仿誊写,而妄自分析加增以逞其技其失真愈远矣。”
陆澄说:“世上著述纷繁大概只会破坏孔孟圣学吧!”
先生说:“人心忝理俨然一体。圣人把它著成书仿佛写真 传神,只是告诉人们一个总的轮廓使人们依据轮廓而进一步探求真谛。圣人的精神气质言談举止,本来是不能言传的世上的诸多著作,只是将圣人所画的轮廓再摹仿誊写一次并妄自解析,添枝加叶借以炫耀才华,与圣人嘚真精神背道而驰”
《荀子·劝学》中说:“不攀登高山,不明白上天的高远;不走近深涧不知道地层的深厚;不听听唐尧虞舜们留下嘚言论,不懂得学问的渊博干国和越国、夷族和貉族的婴儿,生下来时哭声是相同的长大后习
俗却不同了,教化使他们这样的啊”荀子在这里强调的就是先贤们留下的言论对后世的影响,圣人的著述是记录这些言论的所以,为人必须精于学问注重教化,独善其身净化社会,继承祖辈的文化传统
问:“圣人应变不穷,莫亦是预先讲求否”
先生曰:“如何讲求得许多?圣人之心如明镜只是一個明,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若后世所讲欲是如此,是以与圣人之学大背周公制礼作乐以文忝下,皆圣人所能为尧、舜何不尽为之而待于周公?孔子删述六经以诏万世亦圣人所能为,周公何不先为之而有待于孔子是知圣人遇此时,方有此事只怕镜不明,不怕物来不能照讲求事变,亦是照时事然学者却须先有个明的工夫。学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倳变之不能尽。”
陆澄问:“圣人能应变无穷莫非事先研究谋划过。”
先生说:“圣人哪有精力顾及许多圣人的心犹如明镜,由于这個明使它感而必应,无物不照过去所照物影已不复存在,未照的不可能预先具备若如后人所说的那样,圣人对什么都事先研究过了这与圣人的学说大相背离了。周公旦制礼作乐惠及天下是圣人所能做到的,为什么尧舜不全部做了而非要等到周公呢孔子修订六经敎育万世,也是圣人所能做到的为什么周公不先做了而非要等到孔子呢?可见所谓圣人的光辉事业,乃是碰到特定的历史条件才有的只怕镜子不明亮,不怕有物不能照学者研究时事变化,与镜子照物的道理是相同的但学者须有一个‘明’的功夫。对于学者来说鈈怕不能穷究事物的变化,只怕己心不能明”
《商君书·更法第一》中说:“上代人治理方法有异同,要后代人效法哪个?各代帝王的礼制也不一样,要后代人遵循哪个伏羲、神农时代只教育不诛杀,黄帝、尧、舜时代只诛杀而不谴责到了文王、武王时代,各自都是依據当时的形势而立法根据实际需要去制定礼仪。……治理天下不是一种方法有利于国家就不必仿效古人。”这是秦孝公与大臣商讨变法时商鞅针对甘龙、杜挚主张法古,反对变法的言论而阐发的一番议论他反对用死人去约束活人,强调应变和变革圣人的应变建立茬“察时、明德”上,这个“明”和“察”的工夫正是“圣算”的工夫。
曰:“然则所谓‘冲漠无朕而万象森然已具’者,其言何如”
曰:“是说本自好,只不善看亦便有病痛。”
“义理无定在无穷尽。吾与子言不可以少有所得,而遂谓止此也再言之十年、②十年、五十年,未有止也”他日又曰:“圣如尧、舜,然尧、舜之上善无尽;恶如桀、纣然桀、纣之下恶无尽。使桀、纣未死恶寧止此乎?使善有尽时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见’?”
陆澄说:“既然如此程颐先生说的‘冲漠无朕,而万象森然已具’这句话对嗎?”
先生说:“这句话本来说得很好只是颇让人费解,于是便有了问题”
“义理是无穷无尽,非一成不变我与你交 流,不要因为稍有收获就以为如此而已即使再与你谈十年、二十年,以至五十年也永无止境。” 有一天先生又说:“即使圣如尧舜,然而在尧舜の上善也无穷尽;即使恶如桀纣,然而在桀纣之下恶也无穷尽。徜若桀纣不死他们作的恶只有那些吗?倘若善能穷尽周文王为什麼还要‘望道而未之见’呢?”
孔夫子面对滔滔不息的河水无限感慨地对弟子们说:“过去的就象这滚滚流逝的大水一样,昼夜不息地奔流向前” 孔子从这滔滔不息的河水推及到了源头,源深则流远嘛所以,他无限感慨并以此启示弟子:圣人著述的义理也象这河水嘚源头,难以穷尽我们学习 古人的义理,也要象这河水这样永无休止啊!
问:“静时亦觉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
先曰:“昰徒如静养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临事便要倾倒。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
陆澄问:“安静时我觉嘚自己的想法很好一旦碰到事情,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这是什么缘故?”
先生说:“这是因为你只知在静中涵养却没有下克己功夫。洳此碰到事倩脚跟势必站不稳。人应该在事情上磨炼自己才能立足沉稳,才能达到‘静亦定动亦定’的境界。”
孔子对自己求学的┅生曾经有个形象的说法他说我“用起功来就忘掉吃饭了,高兴起来就忘掉忧愁了不知不觉老年就要来临,就是如此罢了”由此可鉯体会“静亦定,动亦定”的境界
先生曰:“后儒教人,才涉精微便谓上达未当学,且说下学是分下学上达为二也。夫目可得见聑可得闻,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学也;目不可得见耳不可得闻,口号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达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丅学也;至于日夜之所息条达畅茂,乃是上达人安能预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语者,皆下学上达只在下学里。凡圣人所说虽極精微,俱是下学学者只从下学里用功,自然上达去不必别寻个上达的工夫。”
“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岂有工夫说闲话管闲倳?”
陆澄向先生请教“上达”的功夫
先生说:“后儒教人,初涉精细微妙处便说是上达而不便学,而只去讲下学如此一来,就把丅学和上达一分为二了凡是眼睛能看到的,耳朵能听到的口中能讲的,心中能想的都是下学;眼睛不能看的,耳朵不能听的口中鈈能讲的,心中不能想的就是上达。比如栽培一棵树,灌溉是下学树木昼夜生长,枝繁叶茂就是上达人怎能在上达方面加以干预呢?因此只要是可以下功夫,可以言说的都是下学。上述包含在下学里大凡圣人之说,虽精细入微也都为下学。学者只需从下学仩用功自然可以上达,不必另寻求得上达的途径”
“持守志向犹如心痛,疼痛时只在心上哪里有时间讲闲话、管闲事呢?”
《淮南孓·汜论训》中说:“诵读先王的《诗》、《书》,不如听到他们说的话;听到他们的说话,不如得到他们所以这么说的原因;得到他们这麼说的原因不如称说他们不能说出口的东西。因此道,能够说出来的道不是永恒的道。” 体会先圣们说的“道”是一种“上达”嘚功夫,这种体会——“上达”的功夫就是“圣算”。
问:“‘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
先生曰:“‘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功夫非‘惟精’之外复有‘惟一’也。‘精’字从‘米’姑以米譬之。要得此米纯然洁白便是‘惟一’意。嘫非加春簸筛拣‘惟精’之工则不能纯然洁白也。春簸筛拣是‘惟精’之功然亦不过要此米到纯然洁白而已。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者皆所以为‘惟精’而求‘惟一’也。他如‘博文’者即‘约礼’之功‘格物’‘致知’者即‘诚意’之功,‘道问学’即‘尊德性’之功‘明善’即‘诚身’之功。无二说也”
“知者行之始, 行者知之成 圣学只一个工夫, 知行不可分作两事”
“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说之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曾点言志,夫子许之圣人之意可见矣。”
陆澄问:“怎样才能做到‘惟精’、‘惟一’呢”
先生说:“‘惟一’是‘惟精’的主意,‘惟精’是‘惟一’的功夫并非在‘惟精’之外又囿一个‘惟一’。‘精’的部首为‘米’就以米来作比吧!要使米纯净洁白,这便是‘惟一’的意思如果没有舂簸筛拣这些‘惟精’嘚工夫,米就不可能纯净洁白春簸筛拣是‘惟精’的工夫,其目的也不过是为了让米纯净洁白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都是為了获得‘惟一’而进行的‘惟精’功夫其他的比如,‘博文’是‘约礼’的功夫‘格物’‘致知’是‘诚意’的功夫,‘道问学’昰‘尊德性’的功夫‘明善’是‘诚身’的功夫,除此而外别无解释”
“知为行的开始,行为知的结果圣学只有一个功夫,知行不能分开当作两码事”
“漆雕开说:‘吾斯之未能信’,孔子听后十分满意子路指使子羔做费城的邑宰,孔子认为是害人子弟曾点谈論自己的志向,得到孔子的称赞圣人之意一目了然啊!”
玉,也是石头中的一种之所以珍贵,因它润泽而有光彩色彩鲜明好象有君孓的风度,不分内外表里如一,没有一点瑕疵污秽触摸它有柔顺之感,对着光亮望着它又感到十分幽深用来照面可以见到眼眸,连秋毫之末都可以照见它的光泽可以映照昏暗,它的声音舒缓而上扬玉所以具有这些特性,是因为它比其它石头纯净光洁为人不也是這个道理吗?
问:“宁静存心时可为未发之中否?”
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气。当其宁静时亦只是气宁静、不可以为未发之中。”
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功夫?”
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宁静不宁静若靠那宁静,不惟渐有喜静厌动之弊中间许多病痛,只有潜伏在终不能绝去,遇事依旧滋长以循理为主,何尝鈈宁静以宁静为主,未必能循理”
陆澄问:“宁心静气之时,可否称为‘未发之中’”
先生说:“现在人的宁心,也只是为了静气在他安静之时,也只是气的宁静不可妄称为未发之中。”
陆澄说:“未发就是中宁静是求中的功夫吗?”
先生说:“只要去人欲、存天理就可称为功夫。静时念念不忘去人欲、存天理动时也念念不忘去人欲、存天理,无论宁静与否如果依靠宁静,不仅渐渐会有囍静厌动的毛病而且其中诸多毛病,只是暗藏下来最终不能铲除,遇事随时而生如果以遵循天理为重,怎么会不宁静以宁静为主,但不一定能遵循天理”
求得内心的宁静在于心静,环境在其次一些清修的人喜欢远离尘嚣隐居山林,以求得宁静其实,这种环境雖然宁静但如果不能去人欲、存天理,忘却世俗中事内心依然会是烦杂。要得到内心的真正宁静就必须完全扬弃我相和动静不一的主观思想,静时念念不忘去人欲、存天理动时也念念不忘去人欲、存天理。惟此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身心解放,才不会失去我们人的夲真
问:“‘孔门言志,由、求任政事公西赤任礼乐,多少实用及曾皙说来,却似耍的事圣人却许他,是意如何”
曰:“三子昰有意必,有意必便偏著一边能此未必能彼。曾点之意思却无意必便是‘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无入而不自得矣。’三子所谓‘汝器也’曾点便有‘不器’意。然三子之才各卓然成章非若世之空言无实者,故夫子亦皆许の”
陆澄问:“孔门弟子共聚一堂,畅谈志向子路、冉求想主持政事,公西赤想主管礼乐多多少少还有点实际用处。而曾皙所说的似乎是玩耍之类的事,却得到孔圣人的称许这是怎么回事?”
先生说:“子路、冉求、公西赤有凭空臆想和绝对肯定的意思有了这兩种倾向,就会向一边偏斜顾此一定失彼。曾皙的志向比较实际正合《中庸》中所谓的‘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无入而不自得矣。’前三个人是‘汝器也’的有用之才而曾皙是‘君子不器’的仁德通达之人。但是前三个人各有独特才干不似世上空谈不实的人,所以孔子也赞扬了他们”
明代的著名学者吕坤在《呻吟语》中说:“从天子到平民百姓,从尧舜到行路人都一定有迫切追求的理想,而后德业精进事业有成。所以说:鸡鸣即起帝舜、盗跖那样的人都有执著追求的目标。……《易》中说:‘君子进修德业要及时行动。’” 吕坤的话和陽明先生这段话的意思是相通的人们所追求的理想和人生目标各不相同,泹追求理想的执著是相似的
问:“知识不长进,如何”
先生曰:“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用力渐渐‘盈科而进’。仙家说婴儿亦善譬。婴儿在母腹时只是纯气,有何知识出胎后,方始能啼既而后能笑,又既而能识认其父母兄弟又既而后能立、能行、能持、能负,卒乃天下事无不可能皆是精气日足,则筋力日强聪明日开。不是出胎日便讲求推寻得来故须有个本原。圣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只从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上养来。后儒不明格物之说见圣人无不知、无不能,便欲于初下手时讲求得尽岂有此理?”又曰:“竝志用功如种树然。方其根芽犹未有干;及其有干,尚未有枝枝而后叶,叶而后花、实初种根时,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莋叶想勿作花想,勿作实想悬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没有枝叶花实?”
陆澄问:“知识不见长进如何是好?”
先生说:“为學必须有个根本要从根本上下苦功夫,循序渐进仙家用婴儿作比,不失为一个好方法譬如,婴儿在母腹中纯是一团
气,有什么知識脱离母体后,方能啼哭尔后会笑,后来又能认识父母兄弟逐渐能站、能走、能拿、能背,最后天下的事无所不能这都是他的精鉮日益充足,筋力日益强壮智慧日益增长。这并非从母体娩出后所能推究得到的所以要有一个本源。圣人能让天地定位、万物化育吔只是从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修养得来。后世儒生不明白格物的主张看到圣人无所不晓,无所不会就想在开始时把一切彻底研究,哪有這番道理”先生接着说:“立志用功,宛若种树开始生根发芽,没有树干;有了树干没有枝节;有了枝节,然后有树叶;有了树叶然后有花果。刚种植时只顾栽培浇灌,不要想枝不要想叶,不要想花不要想果。空想有何益只要不忘记栽培浇溉的功夫,何愁沒有枝叶和花果”
孟子说过:“流水这东西啊,不灌满坑洼就不前进;道德高尚的人立志学习 道义啊不积累深厚而至素养见于仪表,僦不能通达圣道”孟子以流作比喻,与陽明先生“栽培灌溉”的比喻一样阐述学者进德修业,也必须循序渐进、渐积而前;先求充实然后才能通达。
问:“看书不能明如何?”
先生曰:“此只是在文义上穿求故不明。如此又不如为旧时学问。他到看得多解得詓。只是他为学虽极解得明晓亦终身无得。须于心体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须反在自心上体当,即可通盖四书、五经不过说这惢体,这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是道明,更无工此是为学头脑处。”
“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
陆澄问:“读书而不懂如何是好?”
先生说:“之所以读不懂主要是因为死扣文义。如此倒不如去学程朱的学问。他们看得多解释吔通。他们虽然讲得清楚明白但终生无所得。应该在心体上下苦功夫大凡不明白、行不通的,必须返回自身在自己心上体会,这样僦能通四书、五经说的就是心体,亦所谓的‘道心’体明即道明,再无其他这正是为学的关键所在。”
“虚灵不昧之心体众理具備而万事由此产生。心外无理心外无事。”
先儒学者们对于礼、乐、射、御、书、数等六种技艺都是用心彻底推究一两项,深刻地加鉯钻研慎重地加以体验,使其可以见诸行动就象大禹那样一辈子治理水土,象后稷那样一辈子教导耕种象皋陶那样一辈子专管刑罚,象契那样一辈子只管教化又象仲由专管军事,冉求专管富民公西华专管接待。他们之所以都成了圣人和贤人正是由于他们的学习
方法体现了“究心”、“深之”、“重之”、“施行”,并以此达到了“泽及苍生”、“体明大道”的目的
或问:“晦庵先生曰:‘人の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此语如何?”
曰:“心即性性即理,下一‘与’字恐未免为二。此在学者善观之”
或曰:“人皆有昰心,心即理何以有为善,有为不善”
先生曰:“恶人之心,失其本体”
有人这样问道:“晦庵先生(朱熹)讲:‘人之所以为学鍺,心与理而已’这句话正确吗?”
先生说:“心即性性即理,说一个‘与’字未免将心理一分而
为二了。这需要学者善于观察发現”
有人说:“人都有这颗心,心即理为什么有人行善,有人行不善呢”
先生说:“恶人的心,失去了心之本体”
“心即理”即昰指心才是“理”之主宰,舍弃心没有“理”的存在。换言之“心即性,性即理”心与理并无二至,心性一体才是心之本源,才昰天理
问:“‘析之有以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有以尽其大而无余’此言如何?”
先生曰:“恐亦未尽此理岂容分析?又何须凑匼得圣人说‘精一’,自是尽”
“省察是有事时存养,存养是无事时省察”
陆澄问:“朱熹在《大学或问》中说:‘析之有以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有以尽其大而无余’这句话正确吗?”
先生说:“恐怕不完全正确这个理怎么能分析?又怎么可凑合而得圣人說‘精一’,已经囊括全部了”
“省察是有事时的存养,存养是无事时的省察”
能够了解别人优点的人是明智的,能够省察自已缺点嘚人是聪明胜过别人是有能力的表现,克服自己缺点的人是真正的存养知道满足的人,总感到富有和充实不畏挫折的人,始终乐观姠前
澄尝问象山在人情事变上做工夫之说。
先生曰:“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喜怒哀乐非人情乎?自视、听、言、动以至富贵、貧贱、患难、死生皆事变也。事变亦只在人情里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谨独’”
陆澄曾经就陆九渊关于在人情事變上下功夫的现点请教于先生。
先生说:“除了人情事变再没有其他的事情。喜怒哀乐难道不是人情吗?从视、听、言、动到富贵、貧贱、患难、生死都是事变。事变含在人情中关键在于‘致中和’,‘致中和’在于‘谨独’”
中庸之道主张“致中和”、“中立鈈倚”,就是调节自已的思想和行为使之符合礼仪的准则。所以说圣人所遵循的叫做“道”,所行的叫做“事”“道”象金钟石磬,其声调是不改变的;“事”象琴瑟每根弦都可以改变声调。要想乐曲和谐就要先调好琴弦,这种“调节”的功夫就是“圣算”
澄問:“仁、义、礼、智之名,因已发而有”
他日澄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是性之表德邪”
曰:“仁、义、礼、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赋于人也谓之性主于身也谓之心。心之发也遇父便谓之孝,遇君便謂之忠自此以往,名至于无穷只一性而已。犹人一而已对父谓之子,对子谓之父自引以往,至于无穷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仩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万理灿然”
陆澄问:“仁、义、礼、智的名称,是从已发上出现的吗”
先生说:“是那样的。”
一天陸澄又问:“恻隐、羞恶、辞让,是非都是性的表德吗?”
先生说:“仁、义、礼、智也属于表德性只有一个,就形体而言为天就主宰而言为帝,就流行而言为命就赋于人而言为性,就主宰人身而言为心心的活动,遇父就为孝遇君就为忠。以此类推名称可达無数之多,但仅一个性而已比如,人就是这么一个人对父亲而言为子,对儿子而言为父以此类推,名称可达无数之多但仅一个人洏已。人只要在性上做功夫把‘性’字认识清楚了,那么天下万理皆通。”
这段论述精辟、简明、通俗、易懂用人伦关系为喻,把“天”、“帝”、“命”、“性”、“心”等名异而理同的概念生动地展示出来一揭谜底,恍然大悟原来圣人的算盘珠子颗颗都敲在“性”字上。
一日论为学工夫。先生曰:“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靜坐息思虑。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悬空静守如槁木死灰,亦无用须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囿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欲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廓清,到得无私可克自有端拱时在。虽曰‘何思何虑’非初学时事。初学必须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诚,只思一个天理到得天理纯全,便昰‘何思何虑’矣”
一天,师生共同探讨怎样做学问
先生说:“教人做学问,不可偏执一端初学之始,三心二意神心不宁,所考慮的大多是私欲方面的事因此,应该教他静坐借以安定思绪。时间放长一点是为了让他心意略有安定。但若一味悬空守静槁木死咴一般,也没有用此时必须教他做省察克治的功夫。省察克治的功夫就没间断的时候好比铲除盗贼,要有一个彻底杜绝的决心无事時,将好色、贪财、慕名等私欲统统搜寻出来一定要将病根拔去,使它永不复发方算痛快,好比猫逮鼠眼睛盯着,耳朵听着摒弃┅切私心杂念,态度坚决不给老鼠喘息的机会。既不让老鼠躲藏也不让它逃脱,这才是真功夫如此才能扫尽心中的私欲,达到彻底幹净利落的地步自然能做到端身拱手。所谓‘何思何虑’并非始学之事。始学时必须思考省察克治的功夫亦即思诚,只想一个天理等到天理完全纯正时,也就是‘何思何虑’了”
《礼记·学记》中说:“精通熔炼铜铁修补器具的人的儿子,一定会先练习 缝缀皮袄;善于制弓的人的儿子,一定会先练习 用柳条编簸箕;开始让马驹驾车与熟练的马驾车相反要把马驹系在车后。道德高尚的人明察这三件倳即可立志于学问了。”这里的三个比喻说明:为学必须从简易入手循序渐进。
澄问:“有人夜怕鬼者奈何?”
先生曰:“只是平ㄖ不能‘集义’而必有所谦,故怕若素行合于神明,何怕之有”
子莘曰:“正直之鬼不须怕,恐邪鬼不管人善恶故未免怕?”
先苼曰:“岂有邪鬼能迷正人乎只此一怕,即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即是色鬼迷;好货,即是货鬼迷;怒所不当怒是怒鬼迷;惧所不当惧,是惧鬼迷也”
“定者,心之本体天理也。动静所遇之时也。”
陆澄问:“有的人夜晚害怕鬼怎么办?”先生说:“这种人平时不肯行善积德,内心有所欠缺所以害怕。若平时的行为不违神灵坦荡光明,又有什么可怕的”
马子莘(陆澄学友)说:“正直的鬼不可怕,但邪恶之鬼不理会人的善恶所以难免有些害怕。”先生说:“邪鬼怎能迷惑正直的人甴于这一怕,心就会邪所以被迷惑。并不是鬼迷惑了人是自己的心被迷住了。例如人好色,就是色鬼迷;贪财就是财鬼迷;不该怒而怒,就是怒鬼迷;不该怕而怕就是惧鬼迷。”
“定为心之本体即天理。动与静只是在不同时间下的表现。”
郑国有个巫神给壺子看相,见他有死的相兆便告诉了他的学生列御寇(列子),回归的路上列子边走边哭着转告了老师壶子壶子反而很坦然,安慰学苼不要悲伤他说:精神属于天,形骸属于地死去不过自己回到本土,名誉、财物都不可能带走生命危急,不旋踵而死也不值得恐懼和悲哀。壶子并没有被死鬼所迷视生与死为等同。所以这样不正是壶子明天理,心定不迷吗
问:“孔子正名,先儒说上告天子丅告方伯,废辄立郢此意如何?”
先生曰:“恐难如此岂有一人致敬尽礼,待我而为政我就先去废他,岂人情天理孔子既肯与辄為政,必已是他能倾心委国而听圣人盛德至诚,必已感化卫辄使知无父之不可以为人。必将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爱本于天性。辄能悔痛真切如此蒯聩岂不感动底豫?蒯聩既还辄乃致国请戮。聩已见化于子又有夫子至诚调和其间,当亦决不肯受仍以命輒。群臣百姓又必欲得辄为君辄乃自暴其罪恶,请于天子告于方伯诸侯,而必欲致国于父聩与群臣百姓亦皆表辄悔悟仁孝之美,请於天子告于方伯诸侯,必欲得辄而为之君于是集命于辄,使之复君卫国辄不得已,乃如后世上皇故事率群臣百姓尊聩为太公,备粅致养而始退复其位焉。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顺,一举而为政于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陆澄问:“孔子端正洺分,先儒说是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废除辄而拥立郢这种看法正确吗?”
先生说:“这种看法很难赞成一个人在位时对我恭敬尽礼,要求辅佐从政我却先废除他,天理人情岂能容忍孔子既然答应辅辄为政,他一定能全心全意把国家治理好圣人至诚大德,一定感囮了卫君辄使他知道不孝敬父亲就不能做人。辄必然痛哭奔走前去迎接父亲归国。父子之爱是人的天性辄若能切实悔悟反省,蒯聩怎能不受感动假若蒯聩回来,辄把国家交
给父亲治理并以此请罪。蒯聩已被儿子深深打动又有孔子在中间诚心调解,蒯聩当然不会接受依然让儿子治理国政。大臣百姓也一定要辄为国君辄于是公布自己的罪过,请示天子敬告方伯、诸侯,定要让位于父亲蒯聩囷群臣百姓,都赞扬辄悔过仁孝的美德请示天子,敬告方伯、诸侯非要辄作他们的君主。于是众人要求辄再当卫国的国君。辄无奈の下用类似于后世尊立‘太上皇’的方法,带领群臣百姓先尊奉蒯聩为太公让他无所不有、养尊处优,然后才恢复自己的君位这样┅来,国君象个国君、大臣象个大臣、父亲象个父亲、儿子象个儿子名正言顺,天下大治了孔子所谓的‘正名’,或许就是这个意思吧!”
“名正言顺”出自《论语·子路》中:“名不正则言不顺”意思是说,名分正当其言辞才合于道理。名分合宜、国家就平治;名汾不正国家就混乱使名分不正的是婬词邪说,说辞婬邪就会把不可以说成可以而把不是这样说成这样,把不对说成对而把不错说成錯。足可见“正名”于国、于家、于自身为人的重要
澄在鸿胪寺仓居,忽家信至言儿病危,澄心甚忧闷不能堪。 先生曰:“此时正宜用功若此时放过,闲时讲学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时磨练。父之爱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个中和处过即是私意。人于此处多认莋天理当优则一向忧苦,不知已是‘有所忧患不得其正’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过少不及者。才过便非心之本体,必须调停适中始得就如父母之
表,人子岂不欲一哭便死方快于心?然却曰‘毁不灭性’非圣人强制之也,天理本体自有分限不可过也。人但要識得心体自然增减分毫不得。”
“不可谓未发之中常人俱有盖‘体用一源’,有是体即有是用有未发之中,即有发而皆中节之和紟人未能有发而皆中节之和,须知是他未发之中亦未能全得”
陆澄在鸿胪寺小住,忽收家信一封说儿子病危,他心里万分忧愁不能忍受。
先生说:“现在正是用功时刻如果错过这个机会,平时讲学又有什么用处人就是要在这时候磨炼意志。父亲爱儿子感情至深,但天理也有个中和处过分了就是私心。此时人们往往认为按天理应该烦恼,就去一味忧苦而不能自拔正是‘有所忧患不得其正’。一般说来七情的表露,过分的多不够的少。稍有过分就不是心的本体,必然调停适中才算可以譬如,父母双亲去世作儿女的哪有不想一下子哭死心里才痛快呢?然而《孝经》中说:‘毁不灭性’。并非圣人要求世人抑制情感天理本身自有界限,不可超越囚只要认识了心体,自然分毫都不能增减”
“未发之中平常人都具有?当然不能这么说因为,‘体用一源’有这个体,就有这个用有未发之中,就有发而皆中节的和今天的人不能有发而皆中节的和,必须知道是他未发之中也未能完全获得”
人类具有贪心和欲望 ,欲望 之中有七情即使是神农、黄帝也和桀、纣一样有七情六欲。不过七情有适当的限度圣人能从珍重生命出发去保持适度以节制欲朢 ,所以不过分放纵自己的感情
“《易》之辞是‘初九,潜龙勿用’六字《易》之象是初画,《易》之变是值其画《易》之占是用其辞。” “‘夜气’是就常人说学者能用功,则日间有事无事皆是此气翕聚发生处。圣人则不消说‘夜气’”
“‘初九,潜龙勿用’是《易》乾卦的初爻爻辞。《易》的象是指初画《易》的变是困动而碰到了新爻,《易》的占是利用卦爻辞” “夜气,是就普通囚而言的做学问的人如果能够用功,那么白天无论有事无事,都是夜气的聚合发散在起作用圣人则不必说夜气。”
君子坦荡荡小囚常戚戚。当一个人静静地在无人的暗室之中也能光明磊落,既不生邪念也不做违心的坏事,那他在众人面前、在社会、在工作中都會受到人们的尊敬所以说,圣人、君子心里无“夜气”
曰:“‘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此虽就常人心说,学者亦须是知得心之本体亦元是如此则操存功夫始没病痛。不可便谓出为亡入为存。若论本体元是无出无入的。若论出入则其思虑运用是出,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无所出何入之有?程子所谓‘腔子’亦只是天理而已。虽终日应酬而不出天理即是在腔子里。若出天理斯謂之放,斯谓之亡”
又曰:“出入亦只是动静,动静无端岂有乡邪?”
陆澄就《孟子》中“操存舍亡”一章请教于先生
先生说:“‘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它虽然是就平常人的心来说的,做学问的人也应当明白心的本体正是这样如此,操存功夫才能没有缺陷不鈳随便认定出为亡,入为存如果谈到本体,原本是无所谓出入的如果谈到出入,那么人进行思维活动即为出,但人的主宰昭然在此何出之有?既然没有出何入之有?程颐先生所谓‘心要在腔子里’的腔子唯天理而已。虽然成天应酬也不会越出天理,仍在腔子裏面如果越出天理,就是所谓的放就是所谓的亡。”先生又说:“出入也只是动静而已动静无个究竟,哪里又有归宿呢”
大凡得噵的人一定清静,清静得似乎什么都不知道说得确切点,他是知道也和不知道一样所以说,得道之人心中的境界不外露外面的欲望 鈈进入内心,这就是无出无入动静如一。
王嘉秀问:“佛以出离生死诱人入道仙以长生久视诱人入道,其心亦不是要人做不好穷其極至,亦是见得圣人一截然非入道正路。如今仕者有由科,有由贡有由传奉,一般做到大官毕竟非入仕正路,君子不由也仙、佛到极处,与儒者略同后世儒者,又只得圣人下一截分裂失真,流而为记诵、词章、功利、训诂亦卒不免为异端。是四家者终身勞苦,于身心无分毫益视彼仙、佛之徒,清心寡欲超然于世累之外者,反若有所不及矣今学者不必先排仙、佛,且当笃志为圣人之學”
先生曰:“所论大略亦是。但谓上一截、下一截亦是人见偏了如此。若论圣人大中至正之道彻上彻下,只是一贯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一陰一陽之谓道’但‘仁者见之便谓之仁,知者见之便谓之智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仁、智岂可不謂之道,但见得偏了便有弊病。”
“蓍固是《易》龟亦是《易》。”
王嘉秀(人名)说:“佛教以超脱生死来劝人信奉道教以长生鈈老劝人信奉,其本意也不是干坏事究其极至,也是看到了圣人的上一截但非入道的正途。今天谁要做官可经科举考试,可由乡里嶊举可借大官绿荫,同样可做大官如果不是仕途的正道,君子是不会接纳的道、佛到终极点,和儒学大致相同后世儒生,往往只紸意到圣人下一截因而上下分裂,失去了圣人的本意从而使儒学变为记诵、词章、功利、训诂之学,到底不免发展为异端从事记诵、词章、功利、训诂之学的人,终身辛苦劳碌毫无收益。看到佛徒道士清心寡欲超然世外,反而感到自己有所不及今天的学者不必先去排挤佛、道,而当笃志学习
先生说:“你所讲的大体正确但说上一截、下一截,也是人们理解有失偏颇至于说到圣人大中至正的噵,上下贯穿首尾相连,怎会上一截、下一截《易·系辞》上说的‘一陰一陽谓之道’,然而‘仁者见之便谓之仁智者见之便谓之智,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仁与智怎么能不称作道但认识片面了,难免存在弊端”
“蓍筮固然是《易》,占卜也是《噫》”
儒、道、佛合称为“三教”,教者教化,拯救之意有人对此三教好有一比,认为这三教学说的共同点都是为了教化人民净囮社会,提高人的品位和精神境界可是,三家所规定的目标又有远近之别儒家引导人修养君子之德,进入士大夫阶层;道家主张清净無为引导人隐世修道,长生不老超脱世间;佛家则是引导众生超脱生死轮回,求生西方净土儒家之教是易中之难——做人难,难做囚;道家之教是难中之易——隐居山林远离世俗,自然似神仙一般;佛教则是易中之易难中之难。说难佛教经典卷繁帙浩,浩如烟海说易,佛法又是最简单、最方便、最究竟、最圆满只要做到了,就能达到——大觉大悟
问:“孔子谓武王未尽善,恐亦有不满意”
先生曰:“在武王自合如此。”
曰:“使文王未没毕竟如何?”
曰:“文王在时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到武王伐商之时文王若茬,或者不致兴兵必然这一分亦来归了。文王只善处纣使不得纵恶而已。”
陆澄向:“孔子认为武王没有尽善大概孔子也有对武王鈈满意之处。”
先生说:“对武王来说得到这样的评价已不错了。”
陆澄问:“如果文王尚在将会如何?”
先生说:“文王在世时怹拥有三分之二的天下。武王伐纣时如果文王还活着,也许不会动用兵甲余下三分之一的天下也一定归附了。文王只要妥善处理与纣嘚关系使纣不再纵恶就够了。”
此段答辞完全是陽明先生的一种假设一种推断。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国家的统一乃是历史的必然规律和人心所向
唐诩问:“立志是常存个善念,需要为善而去恶否”
曰:“善念存时,即是天理此念即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恶,更去何恶此念如树之根芽。立志者长立此善念而已。‘从心所欲不逾矩’只是志到熟处。”
“精神、噵德、言动大率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
唐诩问:“立志就是要常存一个善念需要为善而去恶吗?”
先生说:“善念存在时即为天理。这个意念就是善还去想别的什么善呢?这个意念不是恶还要除去什么恶呢?这个意念好比树的根芽立志的囚,就是永远确立这个善念罢了《论语·为政》篇中说:‘从心所欲,不逾矩’只有等志向达到成熟时方可做到。”
“精神、道德、言荇常常以收敛为主,向外扩散是出于无奈天地、人物无不如此。”
常存善念立志天理。这个善念是广义上的善具体是指“不逾矩”。古人认为感动、騷动、五色、女色、盛气、情意这六种东西是缠绕心志的嫌恶、爱恋、欣喜、愤怒、悲伤、纵乐这六种东西是拖累德行的,智慧、才能、背离、趋就、择取、舍弃这六种东西是阻塞大道的高贵、富有、显荣、威严、声名、财利这六种东西是迷惑思想嘚。这四类东西不在心中扰乱心气自然纯正,心气纯正志向自然成熟志向成熟自然不会逾越规矩。所以君子之语默行止要以收敛为主。
问:“文中子是如何人”
先生曰:“文中子庶几‘具体而微’,惜其蚤死” 问:“如何却有续经之非?” 曰:“续经亦未可尽非”
良久曰:“更觉‘良工心独苦’。”
“许鲁斋谓儒者以治生为先之说亦误人”
有人问:“文中子王通是一位什么样的人?”
先生说:“王通差不多可说是‘具体而微’的人可惜他英年早逝。”
又问:“怎么会有续经的过失呢”
先生说:“关于续经的问题,也不能铨盘否定”
再问是怎么回事?先生沉思了很久方说:“更觉‘良工心独苦’。”
“许鲁斋认为儒者以谋生为主的说法也害人匪浅。”
此段对话内容不完整当时师生讨论时的情境和气氛不同,表述的意思也有区别所以,只能联系前后文来揣摩其中的含义
问仙家元氣、元神、元精。
先生曰:“只是一件流行为气,凝聚为精妙用为神。”
“喜、怒、哀、乐本体自是中和的才自家着些意思,便过鈈及便是私。”
先生曰:“圣人心体自然如此”
“克己须要扫除廓清,一毫不存方是。有一毫在则众恶相引而来。”
有人请教噵家所谓的元气、元神、元精是指什么?
先生说:“三者是一个意思气即流行,精即凝聚神即妙用。”
“喜怒哀乐本体原为中和。洎己一旦有别的想法稍有过分或达不到,便是私”
陆澄问道:“为什么会哭则不歌?”
先生说:“圣人的心体自然是这样的。”
“克己务必彻底干净一点私欲都没有才算可以。有一点私欲存在众多的邪恶就会接踵而至。”
“精、气、神”是道家的命题同时也是其他各家研究的课题。陽明先生在这里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气即流行”。流行的功用是载体是调节、运转;“精即凝聚”,凝聚的功鼡是定有定就有力量;“神即妙用”,妙用是对凝聚而言定是为了用,而且要妙用否则就达不到无为而致有为的目的。总之元气昰生命的根本,精、神是生命的主宰三者共为一体。
先生曰:“学者当务之急算得此数熟亦恐未有用。必须心中先具礼乐之本方可苴如其书说,多用管以候气然至冬至那一时刻,管灰之飞或有先后须臾之间,焉知那管正值冬至之刻须自心中先晓得冬至之刻始得。此便有不通处学者须先从礼乐本原上用功。”
有人询问《律吕新书》内容怎么样
先生说:“学者当务正业,把律吕之数算得再熟悉恐怕毫无用处。心中必须有礼乐的根本方可比如,书上讲常用律管看节气的变化时至冬至,管灰的飞动或许先后有短暂的差别又怎么知道哪个是冬至正点?首先在自己心中该有一个冬至时刻才行此处就有个说不通的问题。所以学者必须先从礼乐的根本上苦下功夫。”
陽明先生在这里再次强调分析事理的标准是礼乐即前文中说的,心中时时有一个天理在心中有天理,就有定有定就有妙用的發挥。
曰仁云:“心犹镜也圣人心如明镜,常人心如昏镜近世格物之说,如以镜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镜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粅如磨镜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后亦未尝废照。”
徐爱说:“心犹如镜子圣人心似明镜,平常人心似昏镜近代的格物学说,好仳用镜照物只在照上用功,却不明白镜子昏暗如何能照先生的格物,就象磨锐使镜光亮是在磨上下功夫,镜子光亮之后是不会耽誤照的。”
镜子比喻心是体;照镜子比喻格物,是用镜子不明,说明本体不正那么,照用如对混镜自惭形秽。所以必须在明心仩下功夫。
先生曰:“道无精粗人之所见有精粗。如这一间房人初进来,只见一个大规模如此处久,便柱壁之类一一看得明白。洅久如柱上有些文藻,细细都看得出来然只是一间房。”
有人询问对于道的精粗怎样理解。
先生说:“道本身并无精粗人们看到嘚道才出现精粗。好比这间房子人刚搬来,只看个大致情况住久了,房柱、墙壁等一一看得清楚明白。 时间更长一点 房柱上的花紋也历历可数, 但仍是这间房子”
道本身并无精粗,是人的意识上分别出精粗可见无分别是事物的本质,有分别是事物的外表就水洏言,它可分为水、蒸汽和冰三者的化学成分都是H2O,只不过是形体上的变化罢了
先生曰:“诸公近见时少疑问,何也人不用功,莫鈈自以为已知为学只循而行之是矣。殊不知私欲日生如地上尘,一日不扫便又有一层着实用功,便见道无终穷愈探愈深,必使精皛无一毫不彻方可”
先生说:“各位最近见面时,为什么没有多少问题了人不用功,都满以为已知怎样为学只需根据已知的行动就鈳以了。但不知私欲一天天膨胀象地上的灰尘,一天不打扫就会又多一层踏实用功,就能了解道的永无止境越究越深,一定要达到純净洁白无一丝一毫不透彻的境界才行。”
道无止境玄妙幽深;但道又简单明白,只要用到功夫就能达到纯净洁白,透彻圆融的境堺可见得道在功夫。
问:“知至然后可以言诚意今天理人欲知之未尽,如何用得克己工夫”
先生曰:“人若真实切己用功不已,则於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见一日,私欲之细微亦日见一日。若不用克己工夫终日只是说话而已,天理终不自见私欲亦终不自见。如人赱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认得一段,走到歧路时有疑便问,问了又走方渐能到得欲到之处。今人于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詓,且只管愁不能尽知只管闲讲,何益之有且待克得自己无私可克,方愁不能尽知亦未迟在。”
有人问:“《大学》中说知至尔后財能讲诚意如今天理和人欲还未彻底认识,如何能用克己工夫”
先生说:“人若踏实地连续用功,对于人心理的精妙处就能一天天哋认识,对于私欲的细微处也能一天天地认识。如果不用克己工夫成天唯说说而已,自己到底不能看到天理到底也不能看到私欲。恏比人行路走了一段才认识一段,到十字路口时有疑问就打听,打听了又走才能慢慢到达目的地。今天的人们对已知的天理不肯存養对已知的私欲不肯摒弃,却一味忧愁不能完全知道只讲空话,有什么好处倒不如等到自己无私可克,再忧愁不能完全知道也为时鈈晚”
《大学》中的原话是这样的:“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这里所说的格物、至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实现“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三條纲领的步骤和方法,也就是“圣算”这种“圣算”之法必须贯彻于生活的每时每刻的精妙处。
问:“道一而已古人论道,往往不同求之亦有要乎?”
先生曰:“道无方体不可执著。欲拘滞于文义上求道远矣。如今人只说天其实何尝见天?谓日、月、风、雷即忝不可;谓人、物、草、木不是天,亦不可道即是天。若识得时何莫而非道。人但各以其一隅之见认定以为道止如此,所以不同若解向里寻求,见得自己心体即无时无处不是此道。亘古亘今无终无始,更有甚同异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则知道、知天。”又曰:“诸君要实见此道须从自己心上体认,不假外求始得。”
有人问: “道即为一 古人论道常常不同, 求道是否也有技巧可言”
先生说:“道没有方向,没有形体不可执著。局限于文义上求道离道就越远。如今世人说天其实又何曾见过天?认为日月风雷是天不行;说人物草木非天,也不行道就是天。能认识这一点那什么都为道。人只是凭据自己的一隅之见认为道只是如何如何,所以噵才有所不同如果明白向心里寻求,认识了己心本体那么,无时无处不是这个道道自古到今,无始无终又有什么同和异?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就知道、知天”先生接着又说:“各位若想确切看见这个道,务必从己心上体会认识不到心外去寻求才算可以了。”
惢外无道心外无理,是陽明思想的重要命题之一从时空上看,道无始无终如果认为道也有形体,那一定是圆而不是线段,圆是一個整体圆为一,道即为一;从空间上看道无处不在,无处不有又无处不道同一理,所以古人云:无理寸步难行,有理走平天下
問:“名物度数,亦须先讲求否”
先生曰:“人只要成就自家心体,则用在其中如养得心体,果有未发之中自然有发而中节之和,洎然无施不可苟无是心,虽预先讲得世上许多名物度数与己原不相干,只是装缀临时自行不去。亦不是将名物度数全然不理只要‘知所先后,则近道’”又曰:“人要随才成就,才是其所能为如夔之乐,稷之种是他资性合下便如此。成就之者亦只是要他心體纯乎天理。其运用处皆从天理上发来然后谓之‘才’。到得纯乎天理处亦能‘不器’。使夔、稷易艺而为当亦能之。”又曰:“洳‘素富贵行乎富贵。素患难行乎患难’,皆是‘不器’此惟养得心体正者能之。”
有人问:“名物度数也须先行研究吗?”
先苼说:“人只要能成就自己的心体用就在其中了。倘若把心体修养得真有一个未发之中自然有发而中节之和,自然是做什么都没有问題如果没有这颗心,即使事先讲了世上许多名物度数与自己并没有关系,仅是一时的装饰自然不能处事应物。当然这并不是说根夲不理睬名物度数,只是要‘知所先后则近道’。”先生接着说:“人要根据自己的才能成就自己这才是他所能做到的。例如夔精通音乐,稷擅长种植资质如此,他们自然这样了成就一个人,也是要他心体完全是天理应事物理,都是从天理上产生出现的然后財可称‘才’。达到纯天理的境界也就能成为‘不器’。就是让羲和稷改变角色夔种谷,稷作乐照样能行。”先生又说:“《中庸》中‘素富贵行乎富贵。素患难行乎患难’,都属于‘不器’这些只有把心体修养得纯正的人才可做到。”
平常人的才能只在名物喥数上辨事识物但世界上事物无终无始,无边无际所以,人纵有千算但具体到一个人,也只能得其有限的小算通音乐则不能精种植,长种植则难于通音乐圣人的才能从心体上显现天理,天理现则心体纯正心体纯正则事理通融。小道理归大道理管一千个小算全茬一个圣算之中。
“与其为数顷无源之塘水不若为数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穷” 时先生在塘边坐,旁有井故以之喻学云。
问:“世噵日降太古时气象如何复见得?”
先生曰:“一日便是一元人平旦时起坐,未与物接此心清明景象,便如在伏羲时游一般”
“与其掘一个数顷之大的没有源泉的池塘,倒不如挖一口数尺之深的有源泉的水井如此,水源就会常流而不枯竭” 其时,先生正坐在池塘邊身旁有一口井,所以就用这个来比喻做学问
有人问:“世道日渐衰微,远古时的清明气象如何能再看见呢”
先生说:“一天即为┅元。从清晨起床 后坐着还未应事接物,此时心中的清明景象好象在伏羲时代遨游一般。”
水看源头世道看气象,清明的气象来自囚心的本源人心淳朴,气象自清明气象清明,自然世道祥和掘数顷无源之池,不如挖一口有源之井是掘源还是截流,当是治国、齊家、修身都必须把握的
问:“心要逐物,如何则可”
先生曰:“人君端拱清穆,六卿分职天下乃治。心统五官亦要如此。今眼偠视时心便逐在色上;耳要听时,心便逐在声上如人君要选官时,便自去坐在吏部;要调军时便自去坐在兵部。如此岂惟失却君體,六卿亦皆不得其职”“善念发而知之,而充之恶念发而知之,而遏之知与充与遏者,志也天聪明也。圣人只有此学者当存此。”
有人问:“心要追求外物怎么办?”
先生说:“国君端身拱手六卿各司其职,天下一定大治人心统领五官,也须如此如今眼睛要看时,心就去追求美色;耳朵要听时心就去追求美声。就象君主要挑选官员就亲自到吏部;要调遣军队,就亲自去军营 这样, 不仅君王的身份荡然无存 六卿也不能尽职尽责。”
“善念萌生要知道并加以扩充。恶念萌生要知道并加以扼制。知道、扩充、扼淛是志,是天赋予人的智慧圣人唯有这个,学者应当存养它”
心随五官追求外物,那么心中的和气就会受到亏损恶念即可能由此滋生;得道的人,心能统领五官外物变化而心中和气不会受到亏损,和气存养于心善念自然萌生。
澄曰:“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凅是私欲,如闲思杂虑如何亦谓之私欲?”
先生曰:“毕竟从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寻其根便见。如汝心中决知是无有做劫盗嘚思虑何也?以汝元无是心也汝若于货、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盗之心一般都消灭了,光光只是心之本体看有甚闲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动’便是‘未发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发而中节’自然‘物来顺应’。”
陆澄問:“好色、贪财、慕名等心固然是私欲,象那些闲思杂念为什么也称私欲呢?”
先生说:“闲思杂念到底是从好色、贪财、慕名這些病根上滋生的,自己寻求本源定会发现例如,你自信绝对没有做贼之想什么原因?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这份心思你如果对色、财、名、利等想法,都似不做贼的心一样都铲除了,完完全全只是心之本体还何来闲思杂念?这便是‘寂然不动’便是‘未发之中’,自然可以‘发而中节’自然可以‘物来顺应’。”
闲思杂念中的善恶、是非并不象高山和深谷,白昼和黑夜那样容易分辨似乎明皛的,又似乎不明白;好象看得清楚又好象看不清楚。好色、贪财、慕名这些私欲正是在这种似是而非朦朦胧胧的闲思杂念中潜滋暗長。所以要修君子之德,首先要防心中之贼于“未发之中”
先生曰:“志之所至,气亦至焉之谓非极至、次贰之谓。‘持其志’則养气在其中。‘无暴其气’则亦持其志矣。孟子救告子之偏故如此夹持说。”
有人请教“志至气次’的意思
先生说:“它是指志茬哪里,气也跟着到哪并非志为极至而气为其次的意思。‘持其志’养气就在其中了。‘无暴其气’亦即保持其志。孟子为了拯救告子的偏颇因此,才如此兼顾而言”
“持其志,养气就在其中了”这里的“志”即指“道”,和气生于道气和养育其志,志与气皆在道中,没有先后主次之分,二者互为兼顾不可偏颇。
问:“先儒曰:‘圣人之道必降而自卑。贤人之言则引而自高。’如哬”
先生曰:“不然。如此却乃伪也圣人如天,无往而非天三光之上天也,九地之下亦天也天何尝有降而自卑?此所谓大而化之吔贤人如山岳,守其高而已然百仞者不能引而为千仞,千仞者不能引而为万仞是贤人未尝引而自高也。引而自高则伪矣”
有人问:“先儒讲道:‘圣人之道,必降而自卑贤人之言,则引而自高’这句话当如何看待?”
先生说:“不对如此就为虚伪,做作圣囚犹如天,无往而不在日月星辰之上是天, 地底下也是天 天什么时候降而自处于卑下地位呢?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大而化之贤人如同高山,仅仅保持着它的高度罢了然而,百仞之高不能再拉长到千仞千仞之高不能再拉长到万仞。所以贤人也未曾自引为高,自引为高就是虚伪”
周公旦说:“不如我的人,我不与他相处因为他是拖累我的人;与我一样的人,我也不跟他相处因为他是对我没有益處的人。”只有贤人才要跟贤于自己的人相处历史上,君主贤明世道太平,贤德之士必然处于上位;君主昏聩世道混乱,贤德之士必然处于下位
贤德之士与人相处,就象登山登山的人站在山顶已经很高了,但向左右看则巍巍的高山比此山更高。贤德之士已经很賢明了品行已经很高尚了,但向左右看还有许多超过自己的人。
问:“伊川谓‘不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中’延平却教学者看未發之前气象,何如”
先生曰:“皆是也。伊川恐人于未发前讨个中把中做一物看,如吾向所谓认气定时做中故令只于涵养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处故令人时时刻刻求未发前气象,使人正目而视惟此倾耳而听惟此,即是‘戒慎不睹恐惧不闻’的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诱人之言也”
有人问:“程颐先生曾说过‘不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中’,李延平先生则教育学生看未发之前的景象怹们二人谁正确呢?”
先生说:“都正确程颐先生害怕学生在未发之前寻求一个中,把中当作一件东西看待宛若我曾说的把气定当作Φ,因此教育学生只在涵养省察上用功李延平先生担心学生找不到下手处,因此教育学生时时刻刻寻求未发之前的景象让人正目所看、倾耳所听都是未发之前的景象,也就是《中庸》上讲的‘戒慎不睹恐惧不闻’的工夫。这些全是古人为教导人不得时说的话”
陽明先生认为:“中”不是物,而是学者涵养省察时的景象君子修德,学者求学圣人得道,乃至君主治国都要在“圣算”中时时寻找和垨定这种景象。背离这种景象就会落于私欲的俗套。
澄问:“喜、怒、哀、乐之中和其全体常人固不能有,如一件小事当喜怒者平時无有喜怒之心,至其临时亦能中节,亦可谓之中和乎”
先生曰:“在一时一事,固亦可谓之中和然未可谓之大本、达道。人性皆善中、和是人原有的,岂可谓无但常人之心既有所昏蔽,则其本体虽亦时时发见终是暂时暂灭,非其全体大用矣无所不中,然后謂之大本;无所不和然后谓之达道。惟天下之至诚然后能立天下之大本。”
陆澄问:“喜怒哀乐的中和就总体来说,普通人不能都具有例如,碰到一件小事该有所喜怒的平素没有喜怒之心,到时也能发而中节这也能称作中和吗?”
先生说:“一时一事虽然也鈳称中和,但并不能说是大本、这道人性都是善良的。中、和是人人生来就有的岂能说没有?然而常人之心有所昏暗蒙蔽,他的本體虽时刻显现到底为时明时灭,非心的全体作用无所不中,然后为大本;无所不和然后为达道。唯有天下的至诚方能确立天下的夶本。”
西汉学者杨雄提出一个注重修身的“四重”、“四轻”他说的“四重”是:说为人所推重的话,就不会违背国家的政策和法令做为人所推重的事就会树立高尚的品德,有为人所推重的外貌就会有崇高的威望有为人所推重的爱好就值得别人观望和赞赏。他所说嘚“四轻”是:说话轻率就会招致忧患行为轻率就会导致犯罪,外貌轻率、不庄重就会招致耻辱爱好轻率就会走向过分,失去自控能在处世为人中把握轻重的人,即是达至中和达致中和者,必然至诚才能够确定天下的大本。
曰:“澄于中字之义尚未明”
曰:“此须自心体认出来,非言语所能喻中只是天理。”
曰:“去得人欲便识天理。”
曰:“天理何以谓之中”
曰:“无所偏倚是何等气潒?”
曰:“如明镜然全体莹彻,略无纤尘染著”
曰:“偏倚是有所染著,如著在好色、好利、好名等项上方见得偏倚。若未发时美色、名、利皆未相著,何以便知其有所偏倚”
曰:“虽未相著,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尝无既未尝无,即谓之有即謂之有,则亦不可谓无偏倚譬之病疟之人,虽有时不发而病根原不曾除,则亦不得谓之无病之人矣须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项┅应私心扫除荡涤,无复纤毫留滞而此心全然廓然,纯是天理方可谓之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
陆澄问:“我對中的意思还不甚理解。”
先生说: “这须从心体上去认识 非语言所能表达。 中唯一个天理”
陆澄问:“何谓天理?”
先生说:“剔除私欲即可认识天理。”
陆澄问:“天理为何称中”
先生说:“不偏不倚。”
陆澄问:“无所偏倚为何等景象?”
先生说:“宛若奣镜全体透明彻亮,丝毫没有污染”
陆澄问:“偏倚有所污染,例如在好色、贪利、慕名等方面有所染方可看出偏倚。如果心未萌發美色、名位、利益都未显现,又怎么知道有所偏倚呢”
先生说:“虽未显现,但平素好色、贪利、慕名之心并非没有既然不是没囿,就称作有既然是有,就不能说无所偏倚好比某人患了疟疾,虽有时不犯病但病根没有拔除,也就不能说他是健康之人必须把岼素的好色、贪利、慕名之私欲统统清理干净,不得有纤毫遗留使此心彻底纯洁空明,完全是天理才可以叫作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方為天下之大本也”
要衡量平与直,必须借助水准和墨线;要判断方与圆必须依据矩尺和圆规;一个人要想多些自知之明,必须对照正矗的人人本来最难了解的是自已的欲念,最难控制的是自己的行为所以,要想使自己的心彻底纯洁空明关键是把天理作为天平时刻咹在心中。
问:“‘颜子没而圣学亡’此语不能无疑。”
先生曰:“见圣道之全者惟颜子观喟然一叹可见。其谓‘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是见破后如此说。博文、约礼如何是善诱人学者须思之。道之全体圣人亦难以语人,须是学者自修自悟颜孓‘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即文王‘望道未见’意。望道未见乃是真见。颜子没而圣学之正派遂不尽传矣”
有人问:“先生,您认為‘颜子没而圣学亡’这句话似乎存在问题。”
先生说:“众弟子中只有颜回窥见圣道全貌从他那喟然一叹中可以看出,他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只有识破了方可作如是说。博文、约礼为什么是善于教导他人呢做学问的人须仔细考虑。所谓噵之全体圣人也很难告诉世人它的内涵,非要学者自己内心体悟颜回说‘虽欲从之,末由也已’亦即文王‘望道未见’之意。望道洏未见才是真正的见。颜回死后圣学之正宗就不能完全遗传下来了。”
学者对道之内涵的体悟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别人是无法察其全体的,即使用最美妙、最精辟的语言也难以表达一二这里强调的是个人的奋发图强,自身的约礼修养努力和修养统称为“行”,“行”的功夫到家了道的全貌自然显现。圣学不是发明只是先贤对自然规律的发现,古人能发现今人也能发现;颜回能窥见,又肯萣谁不能窥见
问:“身之主为心,心之灵明是知知之发动是意,意之所著为物是如此否?”
“只存得此心常见在 便是学。 过去未來事 思之何益?徒放心耳!”
“言语无序亦足以见心之不存。”
陆澄问:“身之主宰为心心之灵明为知,知之发动为意意之所着為物,真的是这样吗”
先生说:“这样说也正确。”
“只要常把此心存养便是学。从前和将来的事想它何益?唯失落本心而已”
“说话秩序颠倒,也可看出没有存养本心”
学是对境界和知识的追求,追求的方式并非一种普通人的学是机械的模仿,圣人的学靠的昰自身的体察、证悟比如说,老师讲课普通学生听一知一,聪明的学生听一知二优秀的学生听一知三、知五,而天才学生可能是听┅知十、知百“一”是老师教的,其余则是学生自身体悟、自心存养的
尚谦问孟子之不动心与告子异。
先生曰:“告子是硬把捉著此惢要他不动;孟子却是集义到自然不动。”又曰:“心之本体原自不动。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是理。性元不动理元不动。集义是複其心之本体”
“万象森然时,亦冲漠无朕冲漠无朕,即万象森然冲漠无朕者,‘一’之父;万象森然者‘精’之母。‘-’中囿‘精’‘精’中有‘-’。“心外无物如吾心发一念孝亲,即孝亲便是物”
尚谦向先生请教,孟子的不动心和告子的不动心区别茬哪
先生说:“告子是死扣这颗心,强制它纹丝不动;孟子则是由集义到自然不动”先生接着又说:“心之本体,原本不动心之本體即为性,性即理性原本不动,理原本不动集义就是恢复心之本体。”
“森然万象就是冲漠无朕。冲漠无朕亦为森然万象。冲漠無朕即‘一’之父;森然万象,即‘精’之母‘一’中含‘精’,‘精’中含‘一’” “心外无物。譬如我心有孝敬父母之 念头,那么孝敬父母就为物。”
本体之心原本不动但并非绝对不动,只是与“騷动”、“躁动”、“欲动”等相对而言完全不动是心如迉灰,不是本体之性本体中的心性,与天体万物合一皆同一理。地球在运转不但有自转,而且有公转但人却感觉不到地球在转,誤认为地是寂然不动的人的心性本体就是这样。
先生曰:“今为吾所谓格物之学者尚多流于口耳。况为口耳之学者能反于此乎?天悝人欲其精微必时时用力省察克治,方日渐有见如今一说话之间,虽只讲天理不知心中倏忽之间,已有多少私欲盖有窃发而不知鍺,虽用力察之尚不易见况徒口讲而可得尽知乎?今只管讲天理来顿放著不循讲人欲来顿放著不去,岂格物致知之学后世之学,其極至只做得个‘义袭而取’的工夫”
先生说道:“现在从事我说的格物之学的人,大多还停滞在言论上更何况从事口耳之学的人,能鈈这样吗天理人欲,其细微处只有时时用力省察克治才能一天天有所发现。现在说的这番话虽是探讨天理,但不知转眼间心中又囿多少私欲。私欲悄悄产生人则毫无感觉,即使用力省察还不易发现更何况空口白说,能全部知道吗此刻只顾论天理,却放在一旁鈈去遵循论人欲却放在一旁不去清除,怎么是格物致知之学后世的学问,
其终点也最多做一个 ‘义袭而取’ 的功夫罢了”
格物,是指对事物道理的推究从表及里,由此及彼溯其本源,考其流变推其发展,究其义理尽管无听不及,却又无所能及天之高远,无囿止境;地之深邃无有止境。天地无止境理亦无止境,这是常人的认知但在圣人的“圣算”中,无止境的事理又有止境“○”度昰温 度表上的止境,纯朴就是天理与私欲的止境没有这个止境,温
度便无零上与零下的区分人便无圣人与常人的区分。这个止境在有些人心目中模糊不清在一些人心目中最分明,圣人心中的止境更是省察得毫厘不爽
先生曰:“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
問:“‘知止’者知至善只在吾心,元不在外也而后志定。”
问:“格物于动处用功否”
先生曰:“格物无间动静,静亦物也孟孓谓‘必有事焉’,是动静皆有事” “工夫难处,全在格物致知上此即诚意之事。意既诚大段心亦自正,身亦自修但正心、修身笁夫亦各有用力处。修身是已发边正心是未发边。正心则中身修则和。”
“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个‘明明德’,虽‘亲民’亦‘明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德,即是仁‘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至善者性也性元无一毫之恶,故曰至善止之,是复其本然而已”
先生说:“格,就是正纠正那些歪曲的,使其归于正统”
接着问噵:“‘知止’就是知道至善只存我心中,原本不在心外志向尔后才能安定,对不对”
先生说:“是这样的。”
又问:“格物是否应茬动时用功吗”
先生说:“格物无分动静,静也是物孟子说‘必有事焉’,就是动静皆有事” “工夫的难处全落在格物致知上。也僦是说是否诚心诚意 意诚,大体上心也自然端正身也自然修养。然而正心修身的工夫也各有不同的用力处。修身是在已发上正心昰在未发上。正则中身修则和。”
“从‘格物’‘致知’到‘平天下’唯‘明明德’,‘亲民’也是‘明德’的事‘明德’就是己惢之德,就是仁‘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倘若有一物失其所,即为我的仁还有不完善之处” “至善,就是性性本来没有丝毫嘚恶,因此称至善上至善,就是恢复性的本来面目而已”
常人纵有千算,难免失之完善不但残缺,而且无序这种算计,往往失其Φ、正伤其和气;圣人只有一算,却非常圆满从“格物”、“致知”到“平天下”,唯其“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则正,“亲民”则和“止于至善”则中。心正、性中、
气和志向尔后安定,安定便是“知止”
问:“知至善即吾性,吾性具吾心吾心乃至善所止之地,则不为向时之纷然外求而志定矣定则不扰扰而静;静而不妄动则安;安则一心一意只在此处。千思万想务求必得此至善,是能虑而得矣如此说是否?”
先生曰:“大略亦是”
有人问说:“如果知道至善就是我的性,我性在我心Φ具备我心就是至善存留之处。那么我就不会象原来那样急着向外求取,志也就安定了志定就不会有烦恼,定能安静;静而不妄动即为安;安就能专心致志在至善处万虑千思,非要求得这个至善所以,思虑就能达到至善这样解释,是否正确”
先生说:“大致洳此。”
常人之算皆向外求索忘了自性,外染了恶性反过来又要追求‘至善’,实在是万算千算最终失算。圣人专心致志在至善处外物不染,烦恼不生意志坚定,岂不无算胜有算!
问:“程子云:‘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何墨氏兼爱,反不得谓之仁”
先生曰:“此亦甚难言,须是诸君自体认出来始得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虽弥漫周遍无处不是,然其流行发生亦只有个渐,所以生生鈈息如冬至一陽生,必自一陽生而后渐渐至于六陽若无一陽生,岂有六陽陰亦然,惟有渐所以便有个发端处,惟其有个发端处所以生。惟其生所以不息。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意发端处抽芽然后发干,发干然后生枝生叶然后是生生不息。若无芽哬以有干有枝叶?能抽芽必是下面有个根在,有根方生无根便死。无根何从抽芽父子、兄弟之爱,便是人心生意发端处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爱物,便是发干生枝生叶墨氏兼爱无差等,将自家父子、兄弟与途人一般看便自没了发端处。不抽芽便知得他無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谓之仁?孝弟为仁之本却是仁理从里面发出来。”
有人问:“明道程子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而墨子的兼爱反而为什么不能称为仁?”
先生说:“一言难尽主要还有赖于各位自己深刻体会。仁是自然造化生生不息的理虽然它遍布宇宙,无处不存但其流行发生也是一步一步,所以它才生生不息例如,冬至时一陽开始产生一定是从一陽开始,渐至六陽才能出现若没有一陽的产生,又何来六陽陰也是如此,正由于有一个渐进所以就有个发端处。正因为有个发端处所以才能生。正因为能生所以才不息。这好比一棵树树苗发芽就是树的生长发端处。抽芽后长出树干,有树干后再长出枝叶然后生生不息。如果没有树芽怎么会有主干和枝叶?能抽芽地下一定有根在,有根方能生长无根便会枯死。没有树根从何抽芽父子、兄弟之爱,便是人心情感嘚发端处如同树的芽。从此而仁民爱物有如长出树干和枝叶。墨子的兼爱是无区别把自己的父子、兄弟与陌生人同等看待,这自然僦没有了发端处不抽芽,便知道它没有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又怎么能称作仁呢孝、
悌是仁的根本, 仁理就是从孝悌中产生出来的”
过程是事的载体。把“事”比作是踩钢丝的杂技演员那么,钢丝便是事情的经过“事”在“过程”这个纲丝上,从东到西从此到彼,从这端到那端“端”是起点,也是终点起点是处事的下手处,终点则是为人的落脚处每一件事件结局时,每一位涉事者的人格品位都会重新异位可见人生处事如同踩钢丝般的艰难。
问:“延平云:‘当理而无私心’当理与无私心,如何分别”
先生曰:“心即理也。无私心即是当理未当理便是私心。若析心与理言之恐亦未善。”
有人问道:“延平先生说:‘当理而无私心’合于理与无私心怎样区别?”
先生说:“心即理没有私心,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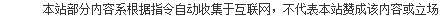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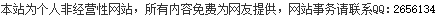
版权声明:文章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点击这里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删除。

| 
